我校省特级专家肖瑞峰教授梳理古代廉政诗歌,深入研究廉政历史文化
9月16日,《钱江晚报》10版、11版以《浙工大教授肖瑞峰最近发论文,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》为题,整版图文报道省特级专家、我校原党委副书记肖瑞峰教授的廉政诗歌研究。
全文转载如下:
浙工大教授肖瑞峰最近发论文,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
李商隐杜甫都是反腐斗士
韩愈还差点豁出性命
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
前不久,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在《浙江社会科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《略议中国古代的廉政诗歌》,梳理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与廉政相关的内容,引起了很多关注。
中国古典诗歌题材广泛,风格多样,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其中有不少关于廉政话题。
“廉政是我们今天提出的概念,在古代,诗人们创作诗歌鞭挞现实,并没有这个意识。”肖瑞峰说。
廉政诗歌对于现实的观照意义,更为突出。“品读这类诗歌,既可以从中得到思想层面的感悟,也可以从中得到艺术层面的熏陶,收获将是双重的。”他认为,加强当下的廉政文化建设,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准绳,但同时也有必要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,包括古典诗歌中,汲取丰富的营养。
《硕鼠》是最早的反腐倡廉作品
在浙江有很多人都听过肖老师的讲座。
梳理廉政诗歌对肖瑞峰来说,一开始是一篇命题作文:他要去省纪委给全体干部做一个讲座,讲讲中国古代有关廉政的诗歌。
肖瑞峰查阅了各地编选的材料后,觉得专业化程度比较低,就自己上手,重新对历代文献做了梳理,前后做了几十场讲座。
2017年,肖瑞峰在总结前几年讲座的基础上,经过打磨,最终形成了这篇聚焦论文。
廉政诗歌这个名字,是后人给它命名的,如果我们追溯一下这些诗歌的源头,你可能会想到一首从小就读过的诗——《诗经·魏风》中的《硕鼠》。
肖瑞峰说,这是最早的反腐倡廉作品,矛头直接指向贪官污吏。为什么“硕鼠”对应的就是统治者?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《毛诗序》里讲到:“硕鼠,刺重敛也。国人刺其君重敛,蚕食于民。不修其政,贪而畏人,若大鼠也。”肖瑞峰说,战国中后期,统治者们横征暴敛,对百姓的剥削越发沉重,窃取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,把自己喂得肥肥的,但又不干正事,治理不好国家。这不就跟偷吃粮食的老鼠一样吗?因此,把统治者比作“硕鼠”,指斥他们凭借权势“窃占”的本意就不言而喻了。
“硕鼠”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比如白居易的《黑潭龙-疾贪吏也》,“不知龙神享几多,林鼠山狐长醉饱”,曹邺的《官仓鼠》,“官仓老鼠大如斗,见人开仓亦不走”。
这首诗还第一次点出了“谁养活谁”的问题。“三岁贯女,莫我肯顾”,意思是说我照顾了你那么多年,供奉给你黍、麦、苗,到头来我却得不到任何回报。肖瑞峰认为这不仅是经济利益上巧取豪夺,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带来了严重摧伤,“笔触直抵人性深处”。
“当然,它还仅仅涉足于反腐的边缘,或者说,还只是意味着廉政诗歌的萌芽。”肖瑞峰说。
诗人用不同方式直指现实
肖瑞峰把古代廉政诗歌的创作特点,分成三类:剖白心志、托古讽今、指陈时弊。
当朝政深陷腐败,有气节的文人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,就写诗表明心迹,显示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,是为“剖白心志”。比如,王昌龄的名句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
肖瑞峰说,它以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比喻此时此刻的自己,实际上是告知亲友自己始终保持着冰清玉洁的本性,表里澄澈,纯洁无瑕,通体透明。“现在,我们要抒写自己廉洁的情怀,依然可以借用这一隽永的诗句。”
批评朝政是有风险的,但读书人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他们“整肃朝纲、匡扶社稷”,便有了委婉曲折的“托古讽今”。
晚唐诗人李商隐《咏史》中有一句经典论断,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”,反对奢侈之风是中国古代所有有识之士都共同主张的,这句话也多次被领导人在讲话中引用。“何须琥珀方为枕,岂得真珠始是车?”李商隐把矛头直指奢靡之风。“何须琥珀方为枕”,说明当时有些官员很会享受,枕头都要琥珀做的。“岂得真珠始是车”,车本来是代步的,为什么一定要镶嵌满珍珠呢?诗的题目是《咏史》,但实际上矛头所向却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追求奢侈生活的腐败分子。
“指陈时弊”则直接将镜头对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。杜甫就是代言人。他的《石壕吏》,直接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。肖瑞峰说,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,他不仅写人民的苦难,也写统治者的腐败。他有3首诗分别叫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潼关吏》,都记录了官僚的腐败,还有《新婚别》、《无家别》、《垂老别》,揭示的是百姓的苦难。他曾经把贫富悬殊、两级分化的现象,概括为令人惊心动魄的诗句: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。”
一封“朝奏”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
“在中国历史上,所有坚持正道的官员对腐败现象和行为都是深恶痛绝的。但受制于历史局限,他们认识不到制度本身的腐败,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制度的意识和勇气。不过,当看到这种腐败行为有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及损害民众利益时,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揭露腐败现象,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。”肖瑞峰说。
他举了一个例子,韩愈的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。
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朝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,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
韩愈是大文豪,但因为给皇帝上书要求革除弊政,触怒了皇帝,遭到贬官。古代贵右贱左,左迁就是贬官。韩愈贬官来到距离京城八千里远的蓝关,写了这首诗给他的侄孙韩湘。
这封“朝奏”就是著名的《论佛骨表》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,元和十三年(818年)十一月,功德使上书给唐宪宗:长安附近的凤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,这个塔每隔三十年开一次,开塔就会保佑大唐国泰民安。
宪宗一听这话,赶紧安排下去,举行各种盛大的“祭祀”典礼,从上到下,一派“疯狂”。韩愈就写了这篇言辞激烈的“朝奏”,宪宗暴跳如雷,要处死韩愈,亏裴度、崔群等一些大臣出来求情。韩愈保住一命,但当晚就被贬往蛮荒之地当刺史。赴任的途中,女儿还死在了路上,“殡之层峰驿旁山下”。
这一年,韩愈已经51岁,他在仕途宦海中几经浮沉,时任刑部侍郎,按理说只要安安心心等退休就行了。但是当他看到劳民伤财的弊政,危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,没有妥协,“欲为圣朝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”。
后来,林则徐的名句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牺牲自我报国的旨意更为显豁,肖瑞峰认为就是由韩愈的这首诗歌演化而来。
从白居易说起,一句诗的背后竟有这么多廉洁细节
老杭州于谦的两袖清风
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官员
细数历朝历代廉政诗歌的创作者,与浙江有关的不在少数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于谦和白居易。
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肖瑞峰的梳理中,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诗歌中所隐含的诸多细节。比如,于谦的“两袖清风”有他所处的时代的背景,也影响了后世的创作;而白居易,则在“惟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的强烈意愿中,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尖锐讽刺和批判。
“在廉政诗歌的创作上,他们两人的视角不一样,于谦以表白心迹为主,白居易则是以揭露弊政为主。”肖瑞峰说。
白居易: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
杭州的“老市长”白居易,在担任杭州刺史时,廉洁奉公,离开杭州了,还将所得工资全数捐出。
50岁,白居易到杭州担任刺史。从上任到长庆四年(824年)五月离任,不到三年,为杭州做了很多实事。
他主持疏浚六井,解决了杭城百姓“喝苦江水”的问题;在西湖边修筑堤防,平时蓄水,旱时放水,减轻了水害,还整理治水的方法和经验,汇成一篇《钱唐湖石记》,供后世当官者参考学习。卸任时,白居易还把节省下来的俸禄都充入公库,作为水利工程的备用基金。
白居易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长大,又在各地当官,深入民间,目睹过民生疾苦,眼里自然容不下腐败。
“在古代,读书人想要改变朝政时局主要有两种方式,一是直接上书给皇帝,如果得不到公正的处置,那么就会选择写文赋诗。”肖瑞峰认为,白居易写下了多首锋芒毕露的反腐诗歌,就是为了让统治者体察老百姓的艰苦,“惟歌生民病,愿得天子知”。
白居易写的《轻肥》,就是个典型例子。
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年)前后,白居易还在天子脚下当官, “拜左拾遗”。“拾遗”,从字面上看,就是捡起遗漏的东西。在唐代,这是言官的一种称谓,“规谏朝政缺失”,也就是专门挑皇帝做得不对的地方,通过劝谏预防决策过失。
“轻肥”一词出自《论语》,指代轻裘肥马的豪奢生活。白居易的这首诗写了一场豪门盛宴,他希望皇帝注意到,在达官权贵中间,存在这样一种奢侈现象,要尽快出台规定,对官员“奢靡之风”有所约束。
在白居易笔下,唐朝那些不遵章守纪的官员,生活奢侈——“意气骄满路,鞍马光照尘。借问何为者,人称是内臣。朱绂皆大夫,紫绶悉(悉,有些版本为“或”)将军。夸赴军中宴,走马去如云。尊罍溢九酝,水陆罗八珍。果擘洞庭橘,脍切天池鳞。食饱心自若,酒酣气益振。是岁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!”
肖瑞峰说,“意气”本来是无形的东西,在白居易笔下却可以洒满道路,可知这些官员骄横到什么地步;尘土本来可以使鞍马黯然失色,而今却是鞍马的光芒照亮了尘土,这又可见他们的鞍马有多么金碧辉煌。
接下来,诗人又用晒食谱的方法,把宴席上的美味佳肴一一曝光,无论酒菜还是水果,无不是价格昂贵。最后笔锋一转,从朝中权臣们吃得酒足饭饱,切换到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旱地衢州: “是岁江南旱,衢州人食人。”当地一片赤土,颗粒无收,老百姓因为极度饥饿,吃完了草根树皮,竟然出现了“人吃人”的人间惨剧。
《新唐书》卷三十五记载:“元和三年,淮南、江南、江西、湖南、广南、山南东西皆旱。四年春、夏,大旱;秋,淮南、浙西、江西、江东旱。”也就是说,从808年到809年,江南等地连年遭受严重旱灾。两句诗点出这天价豪宴不是出现在百姓丰衣足食之后,而是举办在百姓饥寒交迫的大旱之年,两个画面的强烈对比,是白居易对腐败现象的尖锐批判。
“由此可见,这些官员已经穷奢极欲到何等程度。这首《轻肥》诗直陈时弊,揭现实之疮痍,促朝廷之警醒。”
白居易类似的诗作还有《伤宅》《歌舞》《买花》,都收录在《秦中吟十首》组诗中。《歌舞》中“朱轮车马客,红烛歌舞楼”、“岂知阌乡狱,中有冻死囚”,达官贵人在享受奢侈,监狱里有冤魂冻死,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如出一辙。
于谦: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闾阎话短长
杭州人于谦是明朝名臣,官至兵部尚书、少保、太子太傅,都是正二品、从一品的高级职位。
有句谚语说“三年清知县,十万雪花银”,而《明史·于谦传》中却记载,“及籍没,家无余资,独正室鐍钥甚固。启视,则上赐蟒衣、剑器也。”也就是说,于谦蒙冤被抄家,但他家里除了御赐的蟒袍、剑器,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。
“制度本身的腐朽,决定了官员很难保持廉洁。于谦和包拯、海瑞都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官。”肖瑞峰说。
一说到廉政,“两袖清风”一词,会是第一个被很多人想到的词,它与“为官清廉”直接挂钩,这便来自于谦的《入京诗》:“绢帕蘑菇与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,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
明代都穆所著的《都公谭纂》记载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:“于少保尝为兵部侍郎,巡抚河南,其还京日,一物不持。”
当时,于谦还是任职兵部侍郎,主管河南。按照惯例,在外当官的每年年底都要入京述职,下属们都觉得这是一个“跑官要官”的绝佳机会,便建议他带些绢帕、蘑菇与线香作为公关用的“伴手礼”。于谦却断然拒绝,认为这些土产应当“资于民用”,不能用来行贿,败坏官场风气,所以他说:我去朝见天子什么都不带,免得老百姓说闲话。
古人的衣服袖子宽大,不仅可以用来掩面擦汗,还跟百宝箱一样很能装,手帕、钱包、书信都可以放在里面。于谦进京,“一物不持”,自然就是两袖空空,只留清风了。
自从于谦写下《入京诗》,“两袖清风”的风骨一直受到后世尊崇,这个词也经常被引用,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版本。如郑燮的《予告归里,画竹别潍县绅士民》,“乌纱掷去不为官,囊橐萧萧两袖寒,写取一枝清瘦竹,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
昆剧《十五贯》里描写的明代清官况钟,名下也有一首诗,题目很长,《正统四年冬,考满赴京,七邑耆民践送者数百里弗绝,作此口占四首,遍贻耆民以志别》:“清风两袖去朝天,不带江南一寸棉。惭愧士民相饯送,马前酾泪密如泉。”肖瑞峰指出,这首诗并没有收录在古籍文献中,可能只是民间感念于况钟的清廉作风,而好意地把带有“清风两袖”的诗划归到了他的名下,是“一种善意的附会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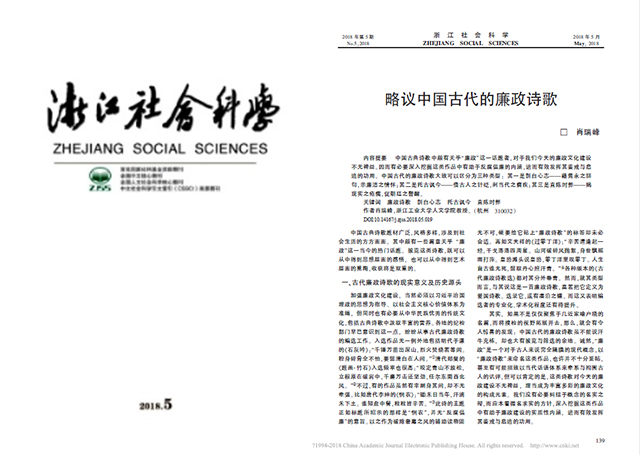
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8年5月刊

《钱江晚报》9月16日10版、11版
《钱江晚报》报道链接:
上一篇:学校举行2018年新教师欢迎大会暨岗前培训活动
下一篇:我校喜迎2018级新生入学报到




